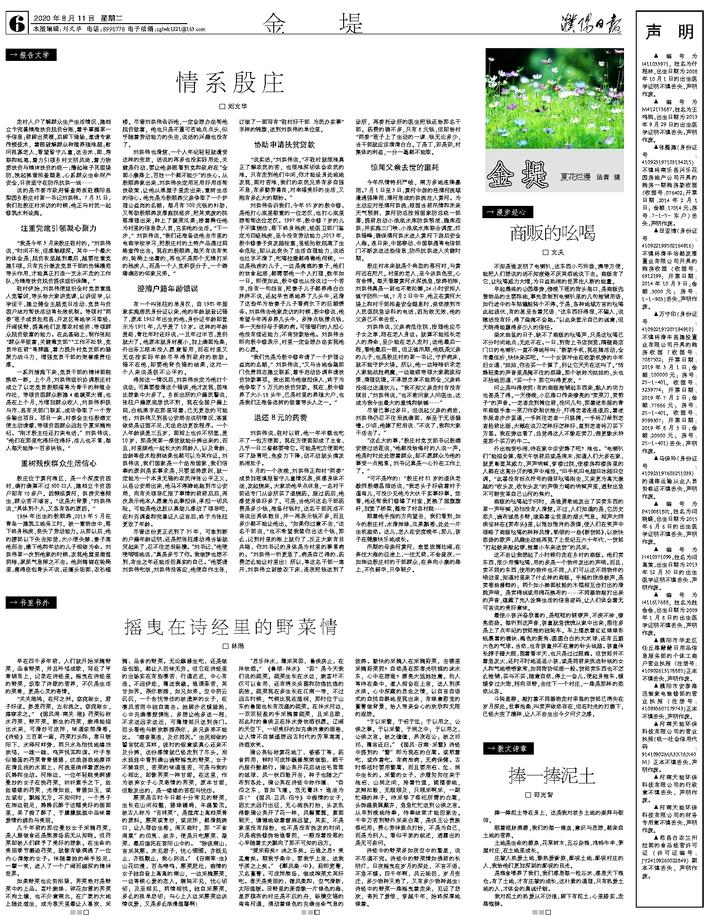不知是谁发明了电喇叭,这东西小巧玲珑,携带方便,能把人们想说的话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地说下去。商贩有了它,让吆喝威力大增,为日益热闹的世界注入新的能量。
早起晨练的公园路旁,傍晚下班的街头巷口,是商贩兜售物品的主要阵地,事先录制到电喇叭里的几句推销用语,如行进中的车轱辘般转个不停。于是,各种地域方言的吆喝此起彼伏,有的甚至含着咒语:“这东西好得很,不骗人,说瞎话没有好,得了偏瘫不会跑。”以此来显示自己的诚意,但天晓得能赢得多少人的信任。
柴米油盐的日子,缺不了商贩的吆喝声,只是这吆喝已不分时间地点,无处不在。一日,到街上书店浏览,隔壁商店门口的电喇叭一直不停地呼叫:“新款手机,现在搞活动,全市最低价,快快来买吧。”一个女孩冲坐在收款机旁的中年妇女道:“姑姑,你去买一个算了,别让它天天在这叫了。”恬静轻柔的声音里是掩不住的烦躁。那个被称为姑姑的,头也不抬地回道:“买一个?那它叫得更欢。”
何止是叫得欢呢!有的商贩推销起东西来,黏人的功力也甚是了得。一天傍晚,小区路口传来嘹亮的“卖菜刀,卖剪子”的声音。一老者走到摊位前,没问几句,那着迷彩服的青年商贩手拿一菜刀作砍削状推介,吓得老者连连退后。着迷彩服者步步紧逼,一手抓住老者一只胳膊,一手将刀举到老者脸前比画,大概在说刀怎样好怎样好,直到老者将刀买下方罢。我在旁边看了,总觉得这人不像在卖刀,倒更像水浒里那个买刀的牛二。
外出饱受吵闹,待在家中该安静了吧?难也。“电喇叭们”能掐会算,每天午饭前后或是周末,知道人们大多在家,就更彰显其威力,声声呐喊,穿楼过院,使楼房和楼房里的人都在这高分贝的噪声中淹没。“旧手机旧电脑旧冰箱旧空调。”此番没有标点符号的循环吆喝刚去,又来更为高亢激越的“收头发,收长头发”的声嘶力竭的呐喊声里,透射出急不可耐变革自己山河的焦灼。
商贩的吆喝起于何时,是谁勇敢地发出了买卖东西的第一声呼喊,恐怕没有人清楚。不过,人们知道的是,它历史悠久,遍布城邑乡野,渲染着尘世里的烟火气息。相声大师侯宝林在《卖布头》里,以惟妙惟肖的表演,使人们在笑声中领略了商贩吆喝的种种风情。郭颂的一曲《新货郎》,以欢快悠扬的歌声,风趣生动地再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货郎“打起鼓来敲起锣,推着小车来送货”的风采。
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行走在乡村的商贩。他们卖东西,很少用嘴吆喝,用的多是一个物件发出的声响。而且,卖不同的东西,使用的物件也不同,人们可从这不同物件的响动里,知道村里来了什么样的商贩。手摇的拨浪鼓声,是卖香油酱醋的;两个如小擀面杖般的木棍相互击打出的清脆声响,是卖棉线或用棉花换布的……不同器物敲打出来的声音,蕴藏了先人诠释生活的信息密码,让人们体会着无可言说的美好意味。
最使小孩兴奋欣喜的,是哐哐的铜锣声,不疾不徐,嘹亮悠扬。每听到这声音,孩童就急慌慌从家中出来,围住多是上了点年纪的货郎推的独轮车。车上摆放着红红绿绿彩纸裹着的糖块、褐色的菱角、圆圆白白的大米球,还有五颜六色的气球。当然,也有孩童并不在意的针头线脑。孩童伸长脖子瞪大眼,围着看半天,也只是过过眼瘾。但货郎并不着急发火,还时不时地逗逗小孩,或是同前来挑选针线的女人和气地唠唠家常,如同街坊邻居一般。货郎卖东西也不怎么推销,买与不买,随意自然,停上一会儿,便起身推车,缓缓穿过大街,拐向田野,去往下一个村庄,一路是那样的悠然从容。
斗转星移,敲打着不同器物走村串巷的货郎已消失在岁月深处。世事沧桑,叫卖声依然存在,但在时光的打磨下,已经大变了模样,让人不由生出今夕何夕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