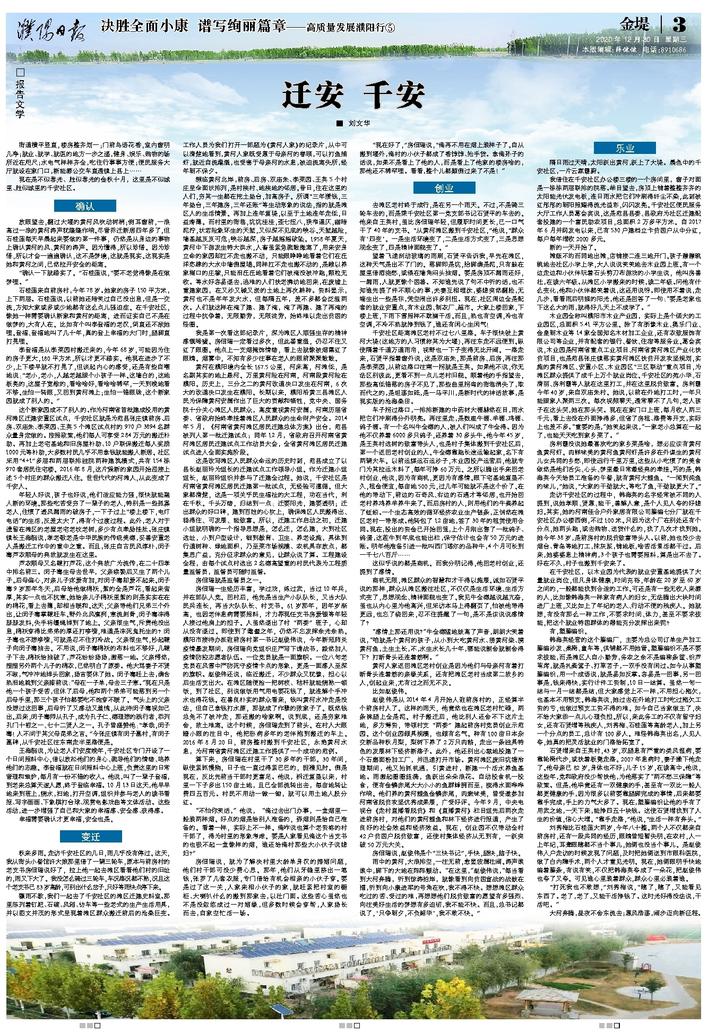街道横平竖直,楼房整齐划一;门前鸟语花香,室内窗明几净;就业、就学、就医的地方一步之遥,健身、娱乐、购物的场所近在咫尺;水电气样样齐全,吃住行事事方便;便民服务大厅就设在家门口,新能源公交车直通镇上县上……
现在是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的金秋十月,这里是不似城里、胜似城里的千安社区。
确认
放眼望去,翻过大堰的黄河风吹动树梢;侧耳窗前,一浪高过一浪的黄河涛声犹隆隆作响。尽管乔迁新居四年多了,但石桂莲每天早晨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仍然是从身边的事物上确认黄河的风、黄河的涛声。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因为珍惜,所以才会一遍遍确认,这不是梦境,这就是现实。这现实是她和黄河之间,已然拉开安全的距离。
“确认一下就踏实了。”石桂莲说,“要不老觉得像是在做梦哩。”
石桂莲来自前房村,今年78岁。她家的房子150平方米,上下两层。石桂莲说,以前她还暗笑过自己没出息,但是一交流,方知大家或多或少地都有这么点儿强迫症。在千安社区,像她一样需要确认新家和黄河的距离,进而证实自己不是在做梦的,大有人在。比如有个叫李登福的老汉,简直还不敌她哩。登福、登福地叫了几十年,真的登上幸福的大门时,腿脚直打晃哩。
李登福是从李菜园村搬迁来的,今年68岁,可能因为住的房子更大,180平方米,所以才更不踏实。他现在进步了不少,上下楼早就不打晃了,但谈起内心的感受,还是有些自嘲地说:“老小,老小,人越老越跟个小孩子一样。这墙白的,这地板亮的,这屋子宽敞的,看啥啥好,看啥啥稀罕,一天到晚地看不够。生怕一转眼,又回到黄河滩上;生怕一错眼珠,这个新家园就成了别人的。”
这个新家园成不了别人的。作为河南省首批建成投用的黄河滩区迁建安置区试点,千安社区就是为范县张庄镇前房、后房、双庙朱、李菜园、王英5个滩区试点村的970 户3894名群众量身定做的。按照政策,他们每人可享受2.84万元的搬迁补助。再加上老宅基地和旧房屋补助、10户联保搬迁每人奖励1000元等补助,大多数村民几乎不用拿钱就能搬入新居。社区采用“4+1”多层和两层联排独院两种建筑模式,共有154栋970套居民住宅楼。2016年8月,这片簇新的家园开始迎接上述5个村庄的群众搬迁入住。世世代代的河滩人,从此变成了千安人。
年轻人好说,孩子也好说,他们适应能力强,很快就能融入新的环境。那些吃苦受穷了一辈子的老人,特别是一些孤寡老人,住惯了透风漏雨的破房子,一下子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反差太大了,得有个过渡过程。此外,老人对于遗留在滩区的老屋老宅老坟老树,多少有点牵肠挂肚。张庄镇镇长王海艇说,孝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妥善安置老人是搬迁工作中的重中之重。而且,张庄自古民风淳朴,闵子骞芦衣顺母的典故就发生在这里。
芦衣顺母又名鞭打芦花,这个典故广为流传,在二十四孝中排名前三。闵子骞生母去世早,父亲续娶后又生了两个儿子。后母偏心,对亲儿子疼爱有加,对闵子骞却爱不起来。闵子骞9岁那年冬天,后母给他做棉袄,絮的全是芦花,看起来蛮厚,其实一点也不抗寒。她给亲儿子棉袄里絮的则是实实在在的棉花,看上去薄,却相当暖和。这天,父亲带他们兄弟三个外出,让闵子骞掌鞭赶车。野外北风凛冽,寒流刺骨,闵子骞冻得瑟瑟发抖,失手将缰绳掉到了地上。父亲很生气,斥责他没出息,棉袄穿得比弟弟的厚还打哆嗦,难道是冻死鬼托生的?闵子骞也不想哆嗦,可就是忍不住打冷战。父亲很生气,抄起鞭子向闵子骞抽去。不用说,闵子骞棉袄的布料也不够好,几鞭子下去,棉袄给抽破了,芦花纷纷扬扬,溅落一地。父亲愕然,捏捏另外两个儿子的棉衣,已然明白了原委。他大骂妻子不贤不淑,气冲冲地掉头回家,扬言要休了她。闵子骞赶上去,满含热泪地跪到父亲膝前说:“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现在只是他一个孩子受苦,但休了后母,他和两个弟弟可能落到另一个后母手里,那三个孩子怕都要吃不饱穿不暖了。气头上的父亲没想过这回事,后母听了又感动又羞愧,从此待闵子骞视如己出。后来,闵子骞师从孔子,成为孔子仁、德理想的践行者,忝列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人之一。孔子曾盛赞他:“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今张庄镇有闵子墓村,有闵子墓碑,从千安社区往东南走半里路便是。
王海艇说,为让老人们安度晚年,千安社区专门开设了一个日间照料中心,借以放松他们的身心、疏导他们的情绪、培养他们的志趣。李登福就在日间照料中心上班,负责这里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每月有一份不错的收入。他说,叫了一辈子登福,到老来总算天遂人愿,终于登临幸福。10月13日这天,他早早地来到班上,烧水,扫地,打开空调,组织并参与老人的读书看报、写字画画、下象棋打台球、观赏电影戏曲等文体活动。这些活动,进一步增强了自己和大家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
幸福需要确认才更幸福,安全也是。
变迁
秋来多雨。走访千安社区的几日,雨几乎没有停过。这天,我从街头小餐馆许大娘那里借了一辆三轮车,原本与前房村的老支书房佃瑞说好了,拉上他一起去滩区看看他们村的旧址的,雨又下大了。我没怎么骑过三轮车,车况路况都不熟,况且这个老支书已83岁高龄,可别出什么岔子,只好等雨快点停下来。
骤雨不歇,我们一起去了千安社区的滩区迁建史料室。那里陈列着钉耙、石磙、风箱、纺车等一些老式的生产生活用具,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呈现着滩区群众搬迁前后的沧桑巨变。工作人员为我们打开一部题为《黄河人家》的纪录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河人家既受惠于母亲河的眷顾,可以打鱼捕虾,就近自流灌溉,也受害于母亲河的水患,被迫流离失所,经年朝不保夕。
濒临黄河北岸,前房、后房、双庙朱、李菜园、王英5个村庄呈伞面状排列,是村挨村、地挨地的邻居。昔日,住在这里的人们,穷其一生都在挖土垫台,加高房子。所谓“三年攒钱,三年垫台,三年建房,三年还账”等生动形象的说法,指的就是滩区人的生活情景。再加上连年复堤,以至于土地连年走低,日益瘠薄。而村里的街巷,坑坑洼洼,歪七扭八,狭窄逼仄,幽暗泥泞,状若险象环生的天堑,又似深不见底的峡谷。天堑越险,墙基越岌岌可危;峡谷越深,房子越摇摇欲坠。1958年夏天,黄河中下游发生特大洪水,人畜虽紧急疏散撤离了,用来安身立命的家园却扛不走也搬不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在汪洋恣肆的大水中墙倒屋塌。同样扛不走也搬不动的,是赖以养家糊口的庄稼,只能泪汪汪地看着它们被淹没被冲跑,颗粒无收。等水好容易退去,逃难的人们扶老携幼地回来,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在又沙又碱又淤的土地上再次耕种。资料显示,黄河也不是年年发大水,但每隔五年,差不多都会泛滥两次。人们就这样在淹了建、建了淹,淹了再建、建了再淹的过程中抗争着,无限勤劳,无限徒劳,始终难以走出贫困的怪圈。
我是第一次看这部纪录片,深为滩区人顽强生存的精神感慨唏嘘。房佃瑞一定看过多次,但此番重温,仍忍不住又红了眼圈。他点上一支烟掩饰情绪,看上去就像被烟熏红了眼睛。烟雾中,不知有多少往事在老人的眼前聚聚散散。
黄河在濮阳境内全长167.5公里,河床高,河滩低,是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河。万里黄河险在河南,河南段黄河险在濮阳。历史上,三分之二的黄河改道决口发生在河南,6次大的改道决口发生在濮阳。长期以来,濮阳沿黄三县滩区人民为保障黄河安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心滩区人民群众,高度重视黄河安澜,河南历届省委、省政府始终牵挂着滩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2014年5月,《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总体方案》出台,范县被列入第一批迁建试点;同年12月,省政府召开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试点工作动员大会,全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试点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这是改写滩区人民群众命运的历史时刻,范县成立了以县长赵丽玲为组长的迁建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作为迁建小组组长,赵丽玲组织并参与了迁建全过程。她说,千安社区是河南省黄河滩区居民迁建第一批试点,无经验可遵循。但大家都清楚,这是一项关乎民生福祉的大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千头万绪,归结到一点:迁要阳光,建要透明;迁出群众的好口碑,建到百姓的心坎上,确保滩区人民搬得出、稳得住、可发展、能致富。所以,迁建工作启动之初,迁建小组就明确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怎么迁,怎么建,大到社区选址,小到户型设计,细到教育、卫生、养老设施,具体到行道树种、绿地面积,乃至菜市场规模、农机具存放点,都集思广益,充分征求群众的意见,让群众说了算。工程建设全程,由每个试点村选出2名德高望重的村民代表为工程质量监督员,监督员可随时监督。
房佃瑞就是监督员之一。
房佃瑞一生经历丰富,学过戏,练过武,当过10年兵,并在部队入党。回村后,他先是当生产小队队长,又当大队民兵连长,再当大队队长、村支书。61岁那年,因年岁渐高,也因老伴患病需要照料,才力荐现任支书房爱银等年轻人接过他肩上的担子。人虽然退出了村“两委”班子,心却从没有退过。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然不忘发挥余光余热。濮阳市接待办派驻前房村第一书记赵俊伟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房佃瑞向党组织庄严写下请战书,毅然加入疫情防控志愿者队伍。一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位八旬老党员在风雪中严防死守疫情卡点的形象,更是一面感人至深的旗帜。赵俊伟还说,临近搬迁,不少群众又犹豫,担心以后生活支出大。在滩区随便捡一把树枝、秸秆就能烧熟一顿饭,到了社区,别说做饭用气用电要花钱了,就连解个手冲水也得花钱。在善良朴实的群众看来,钱叫黄河水冲走是没法,但自己拿钱打水漂,那就成了作孽的败家子了。既然钱总免不了被冲走,那还搬的啥家啊。说到底,还是穷家难舍,故土难离。这个时候,房佃瑞走到了前头。在村人大眼瞪小眼的注目中,他把卧病多年的老伴抱到搬迁的车上。2016年8月20日,前房整村搬到千安社区,永绝黄河水患,为河南省黄河滩区迁建工作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算下来,房佃瑞在村里干了30多年的干部。30年间,纵使紧抓慢挠,日子也一直过得紧巴巴的,捉襟见肘。倒是现在,反比先前当干部时更富足。他说,拆迁复垦以来,村里一下子多出150亩土地,且已全部流转出去,每亩地转让费四五百元。村民不用动一锨一锄,就可以用土地入股分红。
“不怕你笑话,”他说,“俺过去出门办事,一盒烟里一般装两样烟。好点的烟是给别人准备的,孬烟则是给自己准备的。看着一样,实际上不一样。俺咋说也算个老资格的村干部了,得为村里的形象考虑。要是人家看见俺这个当支书的也吸不起一盒像样的烟,谁还给俺村那些大小伙子说媳妇?”
房佃瑞说,就为了解决村里大龄单身汉的婚姻问题,他们村干部可没少费心思。那年,他们从牙缝里挤出一笔钱,张罗了几套衣服,专门借给有机会相亲的小伙子穿。要是过了这一关,人家来相小伙子的家,就赶紧把村室的橱柜、大喇叭什么的搬到那家去,以壮门面。这些苦心虽然也不是没忽悠成过一对姻缘,但多数时候会穿帮,人家扬长而去,自家空忙活一场。
“现在好了,”房佃瑞说,“俺再不用在烟上装样子了。自从搬到堰外,俺村的小伙子都成了香饽饽、抢手货。拿俺孙子的话说,如果不是看上了他的人,而是看上了他家的楼房啥的,那他还不稀罕哩。看看,整个儿都颠倒过来了不是!”
创业
去滩区老村终于成行,是在另一个雨天。不过,不是骑三轮车去的,而是乘千安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石贤平的车去的。他来自王英村,虽比房佃瑞年轻,但履职时间更长,已一口气干了40年的支书。“从黄河滩区搬到千安社区,”他说,“群众有‘四变’。一是生活环境变了,二是生活方式变了,三是思想观念变了,四是精神面貌变了。”
望着飞速刮动玻璃的雨刷,石贤平告诉我,早先在滩区,这种天气是出不了门的。落脚即是坑,抬脚满是泥,只有躲在屋里借酒浇愁,或偎在墙角闷头抽烟。要是房顶不漏雨还好,一漏雨,人就更像个困兽。不知谁先说了句不中听的话,也不知谁先提了件不顺心的事,夫妻互相埋汰,婆媳突然翻脸,无端生出一些是非,凭空闹出许多别扭。现在,社区周边全是配套的就业安置点,有木业园、制衣厂、超市。大家上楼回家,下楼上班,下雨下雪照样不耽搁干活。而且,热也有空调,冷也有空调,不冷不热就挣到钱了,谁还有闲心生闲气!
千安社区距离滩区老村不过七八里路。车子很快驶上黄河大堤(这地方的人习惯称其为大堰),再往东走不远便到。纵使隔着千道万道雨帘,视野也一下子变得无比开阔。一路走来,石贤平指着窗外说,这是双庙朱,那是前房、后房,再往那是李菜园,从前边路口往南一拐就是王英。如果他不说,你无法区别彼此,更看不到一点儿老村旧貌。顺着他的手指望去,那些高低错落的房子不见了,那些曲里拐弯的街巷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坦荡如砥,是一马平川,是新时代的神话故事,是现实版的沧海桑田。
车子拐过路口,一排排新建的中药材大棚赫然在目,雨水把它们冲刷得分外明亮。再往里走,是数座牛棚、羊棚、鸡棚、鸽子棚。有一个名叫牛全德的人,被人们叫成了牛全得。因为他不仅养着6000多只鸽子,还养着30多头牛。他今年45岁,是王英村选树的致富带头人,也是村子集体搬到千安社区后,第一个返回老村创业的人。牛全德靠跑长途运输起家,名下有两辆大车。以前运煤运石运沙子,木业园投产运营后,他就专门为其拉运木料了,每年可挣60万元。之所以腾出手来回老村创业,他说,因为有商机,更因为有感情。眼下宅基地复垦不久,租金便宜,每亩地500元,过几年可能就不是这个价了。在他的带动下,前边的石奇风、右边的石遇才等邻居,也开始回老村养鸡养羊养牛来了。而后房村的人,则用他们的牛粪养起了蚯蚓。一个生态高效的循环经济农业生产链条,正悄然在滩区老村一带形成。他转包了12亩地,签了30年的租赁使用合同。现在,投出的资金已开始回笼,上个月刚出售了一批鸽子、鸽蛋,这茬牛到年底也能出栏,保守估计也会有50万元的进账。明年他准备引进一批叫西门塔尔的品种牛,4个月可长到一千七八百斤……
这似乎说的都是商机。而我分明记得,他回老村创业,还提到了感情。
商机无限,滩区群众的智慧和才干得以施展。诚如石贤平说的那样,群众从滩区搬往社区,不仅仅是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变了,思想观念、精神面貌也变了。我见牛全德越说越亢奋,虽也从内心里为他高兴,但采访本马上得翻页了,怕被他带得更远,也忘了绕回来,忍不住提醒了一句,是不是该说说感情了?
“感情上那还用说?”牛全德猛地拔高了声音,朗朗大笑着说,“咱就是个黄河的孩子,从小到大吃黄河水、捞黄河柴、摸黄河鱼,土生土长,不,水生水长几十年,哪能说割舍就割舍得下?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啊。”
黄河人家返回滩区老村创业是因为他们与母亲河有着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缘关系,还有把滩区老村当成第二故乡的人,创起业来,尤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赵俊伟。
赵俊伟是从2014年4月开始入驻前房村的,正经算半个前房村人了。这样的雨天,他竟然也在滩区老村忙碌,两条裤腿上全是泥。村子搬迁后,他比别人还舍不下这片土地,多方筹资,带领村支“两委”建起前房村党员创业示范园。这个创业园颇具规模,也颇有名气。种有100亩日本杂交新品种秋月梨,梨树下养了2万只肉鹅,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林下经济新路子。此外,他还别出心裁地投建了一个石磨面粉加工厂,并迅速打开市场。黄河滩区废旧坑塘治理期间,他又抢抓机遇,引黄进村,新建一个活水养鱼基地。雨溅起圈圈涟漪,鱼跃出朵朵浪花。自动投食机一投食,便有金鳞赤尾大大小小的鱼群蜂拥而至,搅得水面哗哗作响。他们养的黄河鲤鱼金鳞赤尾,肉嫩味美,曾受邀参加河南省脱贫攻坚优秀成果展,广受好评。今年9月,中央电视台《走村直播看脱贫》和《直播黄河》栏目组先后两次走进前房村,对他们的黄河鲤鱼和林下经济进行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现在,创业园不仅带动全村42户贫困户脱贫致富,还使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一跃突破50万元大关。
房佃瑞说,赵俊伟是个“三快书记”,手快,腿快,脑子快。
雨中的黄河,大浪排空,一往无前,愈显波澜壮阔。涛声滚滚中,脚下的大地在阵阵颤动。“在这里,”赵俊伟说,“每当看到大河奔腾,听到惊涛拍岸,就像看到向贫困宣战的战鼓在擂,听到向小康进军的号角在吹,我不得不快。想想滩区群众吃过的苦、受过的难,再想想他们脱贫致富的愿望有多强烈、向往美好生活的梦想有多迫切,我不能不快。而且,总书记都说了,‘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我不敢不快。”
乐业
隔日雨过天晴,太阳跃出黄河,跃上了大堤。晨色中的千安社区,一片云蒸霞蔚。
我借住在千安社区办公楼三楼的一个房间里,窗子对面是一栋栋两层联排的院落。举目望去,房顶上铺着整整齐齐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连日雨水把它们冲刷得纤尘不染,此刻被红彤彤的朝阳照耀得流光溢彩,闪闪发亮。千安社区便民服务大厅工作人员葛会宾说,这是范县县委、县政府为社区迁建配套投建的一个富民助农项目,总面积2万多平方米。自2017年6月并网发电以来,已有53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从中分红,每户每年增收2000多元。
新的一天开始了。
摊贩不约而同地出摊,店铺接二连三地开门。孩子蹦蹦跳跳地去社区小学上学,大人说说笑笑地去木业园上班。有一个边走边和小伙伴玩着石头剪刀布游戏的小学生说,他叫房善壮,在读六年级。从滩区小学搬来的时候,读二年级。问他有什么变化,他和小伙伴都笑着说,这还用说呀。即使用不着说,走几步,看看雨后明媚的阳光,他还是回答了一句:“要是老家也下这么大的雨,就得好几天上不成学了。”
木业园全称叫濮阳市木业产业园,实际上是个偌大的工业园区,总面积5.41平方公里。除了有浙豫木业、奥乐门业、金皇朝木业等14家全国知名木材加工企业,还有衣致服饰有限公司等企业,并有配套的银行、餐饮、住宿等服务业。葛会宾说,木业园是河南省重点工业项目、河南省黄河滩区产业化扶贫项目,也是范县张庄镇落实黄河滩区扶贫开发攻坚规划,实施的黄河滩区、安置小区、木业园区“三区联动”重点项目,为滩区群众提供了成千上万个就业岗位。千安社区的苑小华、石清丽、房利霞等人就在这里打工,并在这里脱贫致富。房利霞今年40岁,来自双庙朱村。她说,以前在外地打工时,一年只能跟家人聚两三次。每次视频聊天,通常聊不了几句,老人孩子在这头哭,她在那头哭。现在在家门口上班,每月收入两三千元,看上去没在外面挣得多,但省了房租、路费等开支,实际上也差不多。“重要的是,”她笑起来说,“一家老小总算在一起了,也能天天吃到家乡菜了。”
房利霞没说她最喜欢吃的家乡菜是啥,想必应该有黄河鱼黄河虾。肉鲜味美的黄河鱼黄河虾是许多在外谋生的黄河儿女共同的乡愁,即使远行千里万里,这些从小吃惯了的美食 依然是他们舌尖、心头、梦里最日常最经典的牵挂。巧的是,韩海英今天给员工准备的午餐,就有黄河大鲤鱼。“一闻到炖鱼的味儿,”她说,“大家的干劲就大。等吃了鱼,干劲就更大了。”
走访千安社区的过程中,韩海英的名字经常被不同的人提到,说她孝顺、贤惠、能干,善解人意,是个人见人夸的好媳妇。其实,她的河南佳合户外家居有限公司藤编七分厂就在千安社区办公楼西侧,不过100米。只因为这个厂在别处还有个分点,她两头跑,或去购物、送货什么的,找了几次才找到她。她今年38岁,是前房村的脱贫致富带头人。以前,她也没少去烟台、青岛等地打工,抹灰浆,铺地板,啥苦活累活都干过。后来,她婆婆患上精神病,3个孩子也需要照料,算是出不去了。好在不久,村子也搬到千安来了。
在千安社区,以木业园为代表的就业安置基地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但凡身体健康,时间充裕,年龄在20岁至60岁之间的,一般都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可还是有一些无收入来源的人,比如像韩海英一样家有病人的妇女,无法腾出大块时间进厂上班,又比如上了年纪的老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她就想,有没有那么一种工作,不要求时间、体力,甚至不要求技能,把这个就业特困群体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呢?
有,塑藤编织。
韩海英经营的这个藤编厂,主要为总公司订单生产加工藤编沙发、桌椅、童车等,供销都不用她管。塑藤编织不是不要求技能,而是滩区人自小勤劳,务农之余不是编柳条筐、织芦苇席,就是扎粪箕子、打草苫子,一双手没有闲过。如今从事塑藤编织,用一个成语说,就是易如反掌。容易是一回事,另一回事是,钱来得快,实行计件工资制,10日一结算。虽然一旬一结与一月一结都是结,但大家感觉上不一样,不用担心拖欠,也基本不用预支。韩海英说,她过去在外地打工时吃过拖欠工资的亏,也做过预支工资不得的难。如今自己当家做主了,决不给大家添一点儿心理负担。所以,来此务工的不仅有留守妇女,还有石贤增等残疾人,刘秀梅、石桂莲等高龄老人。加上另一个分点的员工,总计有100多人。难怪韩海英出名,人见人夸,她真的把灵活就业的门路给拓宽了。
石贤增来自王英村,43岁,双腿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要靠轮椅代步,或扶着板凳走路。2007年患病时,妻子撇下他走了。他母亲已82岁,身体也不好;儿子15岁,在读高中。他说,这些年,党和政府没少帮扶他,为他落实了“两不愁三保障”等政策。但是,他毕竟还有一双健康的手,甚至有一双比一般人都更健康的手,因为很多以前要靠腿脚完成的事情,后来都要靠手完成,手上的力气大多了。现在,塑藤编织让他的手有了用武之地,一天下来,能挣四五十块钱。这使石贤增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信心大增。“靠手走路,”他说,“生活一样有奔头。”
刘秀梅比石桂莲大两岁,今年八十整。两个人不仅都来自前房村,还有一段共同的经历,眼睛曾短暂失明。在农村,人一上年纪,耳聋眼瞎都不当个事儿,她俩也没当个事儿。是赵俊伟入户走访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及时把她俩送到市眼科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两个人才重见光明。现在,她俩眼明手快地编着藤条,有说有笑,不仅把韩海英夸成了一朵花,把赵俊伟也夸了又夸。可见谁心里装着群众,群众心里必装着谁。
“打死我也不敢想,”刘秀梅说,“瞎了,瞎了,又能看见东西了。老了,老了,又能干活挣钱了。这时光好得没法说,干活吧。”
大河奔腾,昼夜不舍东流去;惠风浩荡,阔步迈向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