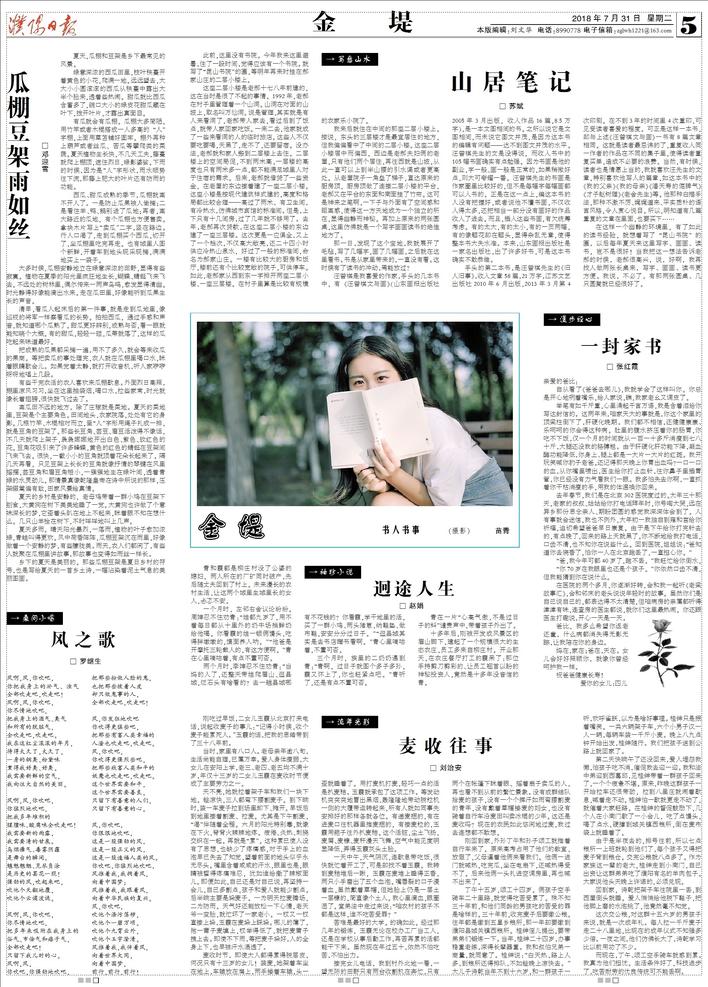此前,这里没有书院。今年我来这里避暑,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应该有一个书院。就写了“昆山书院”的匾,等明年再来时挂在郝家山庄的二层小楼上。
这座二层小楼是老郝十七八年前建的,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1992年,老郝在村子里管理着一个山洞。山洞在对面的山坡上,取名叫万仙洞。说是管理,其实就是有人来看洞了,老郝带人家去,看过后到了饭点,就带人家回家吃饭。一来二去,他家就成了一些来看洞的人的临时旅店。这些人不仅要吃要喝,天黑了,走不了,还要留宿。没办法,老郝就和家人搬到二层楼上去住。二层楼上的空间局促,不到两米高,一层楼的高度也只有两米多一点,都不能满足城里人对于住宿的需求。后来,老郝就借贷了一些资金,在老屋的东边接着建了一座二层小楼。这座小楼是按现代建筑样式建的,高度和格局都比较合理——高过了两米,有卫生间,有冷热水,仿佛城市宾馆的标准间。但是,上下只有十几间房,过了几年就不够用了。去年,老郝再次贷款,在这座二层小楼的东边建了一座三层楼。这次更是一应俱全,又上了一个档次,不仅高大敞亮,还二十四小时供应冷热山泉水,好过了一般的标准间,命名为郝家山庄。一楼有比较大的厨房和饭厅,楼前还有个比较宽敞的院子,可供停车。如此,老郝家从西到东一字排开两座二层小楼、一座三层楼。在村子里算是比较有规模的农家乐小院了。
我来后就住在中间的那座二层小楼上。按说,东头的三层楼才是最宜居住的地方,但我偏偏看中了中间的二层小楼。这座二层小楼居中而偏西,西边是老郝夫妇俩的老屋,只有他们两个居住,再往西就是山坡,从此一直可以上到半山腰的引水渠或者更高处。从老屋院子一角垒了梯子,直达原来的厨房顶,厨房顶做了连接二层小楼的平台,老郝又在平台的东面和南面挂了竹帘。这可是神来之笔啊,一下子与外面有了空间感和距离感,使得这一方天地成为一个独立的所在,显得幽静而神秘。再加上原来的两张圆桌,这里仿佛就是一个写字画画读书的绝佳地方了。
那一日,发现了这个宝地,我就展开了毛毡,写了几幅字,画了几幅画,之后就在这里看书。书是从家里带来的,一直没有看。这时候有了读书的冲动,焉能放过?
汪曾祺是我喜爱的作家,手头的几本书中,有《汪曾祺文与画》(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收入作品16篇,8.5万字),是一本文图相间的书。之所以说它是文图相间,而未说它图文并茂,是因为这本书的编辑有问题——达不到图文并茂的水平。汪曾祺先生的文是没得说,而收入书中的105幅书画确实有点勉强。因为书画是他的副业,字一般、画一般是正常的,如果稍微好点,则大可夸耀一番。汪曾祺先生的书画是作家圈里比较好的,但不是每幅字每幅画都可以入书的。正是在这一点上,编这本书的人没有把握好,或者说他不懂书画,不仅收入得太多,还把相当一部分没有画好的作品收入了进去。而且,插入这些书画,有欠统筹考虑。有的太大,有的太小,有的一页两幅,有的像题花却在题头,显得杂乱无章,使得整本书大失水准。本来,山东画报出版社是一家名出版社,出了许多好书,可是这本书确实不敢恭维。
手头的第二本书,是汪曾祺先生的《旧人旧事》,收入文章58篇,21万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2013年3月第4次印刷。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4次重印,可见受读者喜爱的程度。可正是这样一本书,却与上述《汪曾祺文与画》一书有8篇文章相同。这就是读者最忌讳的了,重复收入同一作者的作品在不同的集子里,使得读者重复买单,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当然,有时候,读者也是情愿上当的,我就喜欢汪先生的文章,特别喜欢他写人的篇章,如这本书中的《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潘天寿的倔脾气》《才子赵树理》《老舍先生》等。他那种白描手法,那种不激不厉、娓娓道来、平实质朴的语言风格,令人赏心悦目。所以,明知道有几篇重复的文章在里面,也要买下……
在这样一个幽静的环境里,有了如此的读书经验,就想着写了“昆山书院”的匾,以后每年夏天来这里写字、画画、读书,岂不是很好!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老郝的时候,老郝很高兴,说,好啊,我再找人做两张长桌来,写字、画画、读书更方便。我说,不必了,有那两张圆桌、几只圆凳就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