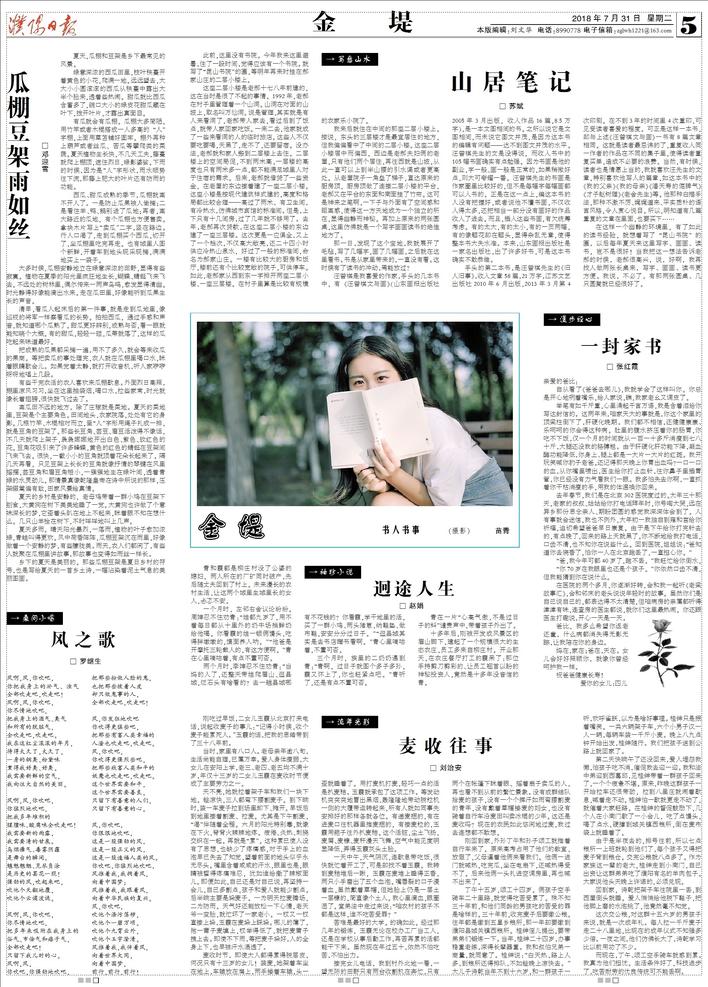刚吃过早饭,二女儿玉霞从北京打来电话,说起收麦子的事儿:“记得小时候,收个麦子能累死人。”玉霞的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三十八年前。
当时,家里有八口人。老母亲年逾八旬,生活尚能自理,已属万幸。爱人身体瘦弱,大女儿在安阳上学,老三、老四、老五均不满十岁,年仅十三岁的二女儿玉霞在麦收时节便成了主要劳力之一。
天不亮,她就拉着架子车和我们一块下地。趁凉快,三人都弯下腰割麦子。到下晌时,装一车麦子拉到场里卸下、摊开。早饭后到地里接着割麦、拉麦。尤其是下午割麦,“渴”伴随着全程。六月的阳光特别毒,就像在下火,脊背火辣辣地疼。疲倦、炎热、刺挠交织在一起。再就是“累”。这种累已使人没有了思想,也缺少了疼痛感,对于手上的血泡早已失去了知觉,望着前面的地头似乎永无尽头。嘴里含着咸咸的汗水,眼里也是,眼睛被蜇得疼痛难忍,犹如谁给撒了辣椒面儿。即便如此,自己还是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会儿,自己多割点,孩子和爱人就能少割点。后半晌主要是垛麦子。一为明天拉麦腾场,二为防雨。天气好还能放松一下心情,老天爷一变脸,就忙坏了一家老小。一杈又一杈直接上垛,玉霞在麦垛上踩垛。哪儿的薄了,抱一莆子麦填上,杈举得低了,就把麦莆子拽上去。即使不下雨,等把麦子垛好,人的全身上下,也早被汗水溻透了。
麦收时节,即使大人都得累得脱层皮,何况只有十三岁的女儿!装麦,她架着车坐在地上,车辕放在肩上,两手搂着车辕,头一歪就睡着了。用打麦机打麦,轻巧一点的活是扒麦秸。玉霞就承包了这项工作。等发动机突突突地冒出黑烟、轰隆隆地带动脱粒机一侧的大履带运转起来,所有人就如同事先安排好的那样各就各位。有递麦捆的,有在进麦口往机器里推麦捆的,有接麦粒的,玉霞用筢子往外扒麦秸。这个活脏,尘土飞扬,麦屑、麦糠、麦秆漫天飞舞,空气中能见度明显降低,弄得玉霞灰头土脸。
一天中午,天气阴沉,连歇息带吃饭,很快就忙着开工了,可是却找不着玉霞。我转到麦秸堆后一瞅,玉霞在麦堆上睡得正香,两只小手磨出了五个血泡。嘴唇裂的口子浸着血,虽然戴着草帽,但她脸上仍是一层土一层糠的,简直像个土人。我心里滴血,眼圈湿了。堂弟法中走过来说:“咱农村的孩子不都是这样,谁不吃苦受罪?”
苦难是最好的大学。的确如此。经过那几年的锻炼,玉霞无论在校办工厂当工人,还是在学校从事后勤工作,再苦再累的活都能干下来。虽然现在年过五十,依然不怕吃苦,不怕出力。
接完女儿电话,我到村外北地一看,一望无际的田野只有两台收割机在奔忙,只有两个在帐篷下眯着眼、摇着扇子卖瓜的人,再也看不到从前的繁忙景象。没有成群结队拾麦的孩子,没有一个个挥汗如雨弯腰割麦的青年,没有戴着草帽搂麦的妇女,也没有骑着自行车沿麦田叫卖冰棍的少年。这还是麦收吗?现在的农民如此悠闲地过麦,我过去连想都不敢想。
刚回到家,外孙丁午和孙子颂工就推着自行车来了。原来高考占用了他们的教室,放假了,父母逼着他俩来看我们。他俩一进门就喊热,吃完瓜,坐在电扇下,还喊热得受不了。后来他俩一头扎进空调房里,再也喊不出来了。
丁午十五岁,颂工十四岁。俩孩子空手骑车二十里路,就觉得吃苦受累了。殊不知三十年前,和他们同龄的男孩吃的苦受的罪是啥样的。三十年前,收完麦子后要缴公粮。往年都是缴到五星乡粮所,那一年却要缴到濮阳县城关镇西粮所。桂绅侄儿提出,要带弟弟们锻炼一下。当年,桂绅二十四岁,办事稳重老练,深得长辈器重。我和叔伯兄弟一商量,就同意了。桂绅说:“白天热,路上人多,到粮所还得排队,不如趁晚上凉快去。”大儿子诗乾当年不到十六岁,和一群孩子一听,欢呼雀跃,以为是啥好事哩。桂绅只是抿着嘴笑。一共六辆架子车,六个小男子汉一人一辆,每辆车装一千斤小麦。晚上八九点钟开始出发,桂绅随行。我们把孩子送到公路上就回家了。
第二天快晌午了还没回来,爱人埋怨我懒,怕孩子吃不消,催促我去迎一迎。我和法中弟迎到西葛邱,见桂绅带着一群孩子回来了,一个个疲惫不堪。原来,昨晚这群孩子一开始拉车还很带劲,拉到八里庄就闹着歇息,喊着走不动。桂绅怕一歇就更走不动了,就催着大家赶路。在桂绅的督促鼓励下,几个人在小南门歇了一小会儿,吃了点馒头,喝了点水,硬撑到城关镇西粮所,倒在麦布袋上就睡着了。
由于是半夜去的,排号往前,所以七点粮所一上班就轮到他们了,每个孩子又得把麦子背到粮仓。交完公粮就八点多了。作为家族这一辈的老大,桂绅走到小南门,自己出资让这群弟弟吃了濮阳有名的羊肉包子。大家说他头天晚上许诺的,必须兑现。
回到家,诗乾把架子车往院里一丢,到西屋倒头就睡。爱人悄悄给他脱下鞋子,把他脚上磨的水泡挑了,他竟然毫不知觉。
这次交公粮,对这群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来说,就是一次成年礼。每人拉一千斤麦子走二十八里地,比现在的成年仪式不知强多少倍。一夜之间,他们仿佛长大了,诗乾学习比以前用功了不少。
而现在,丁午、颂工空手骑车就感到累。我真为他们担忧。生活条件好了,科技进步了,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可不能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