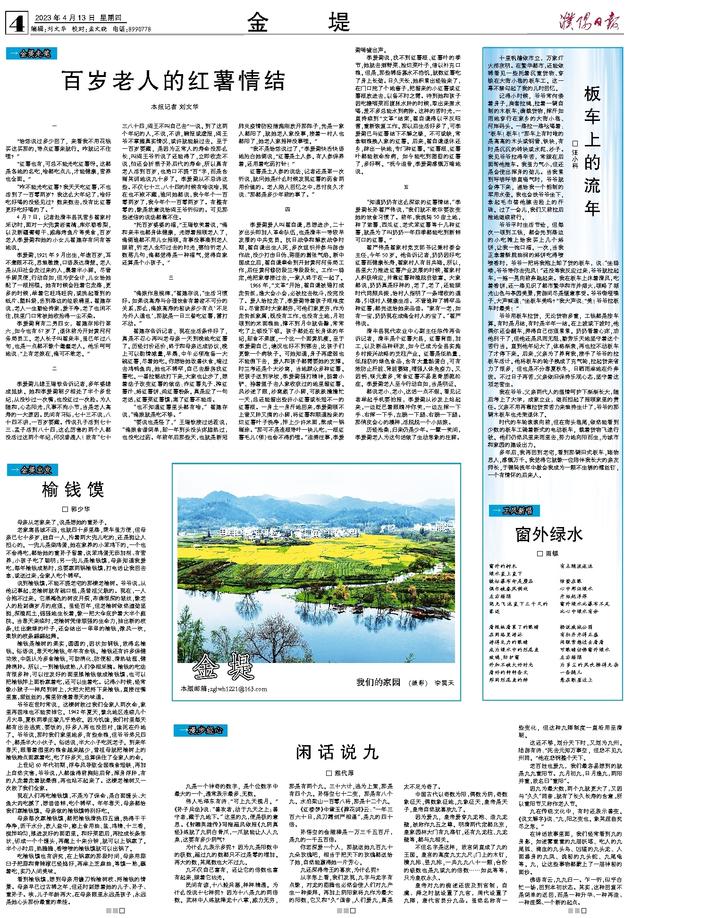母亲从老家来了,说是想她的重孙子。
老家离县城不远,也就四十多里路,乘车虽方便,但母亲已七十多岁,独自一人,拎着两大兜儿吃的,还是挺让人担心的。一兜儿是柴鸡蛋,她在家养的小笨鸡下的,一个也不舍得吃,都给她的重孙子留着,说笨鸡蛋无添加剂、有营养,小孩子吃了聪明;另一兜儿是榆钱馍,母亲知道我爱吃,每年榆钱成熟时,总要蒸两锅榆钱馍,打电话让我回去拿,或送过来,全家人吃个稀罕。
说到榆钱馍,不能不提老宅的那棵老榆树。爷爷说,从他记事起,老榆树就有碗口粗,是曾祖父栽的。现在,一人合抱不过来。它黑褐色的树皮开裂,布满很深的皱纹,像老人的脸刻满岁月的疤痕。虽经百年,但老榆树依然遒劲坚挺,深植泥土,倔强地生长着,像一把大伞庇护着大半个庭院。当春天来临时,老榆树凭借顽强的生命力,抽出新的枝条,吐出嫩绿的叶子,还会结出一串串的榆钱,微风一吹,柔软的枝条翩翩起舞。
榆钱是榆树的果实,圆圆的,因状如铜钱,故得名榆钱。俗语说,春天吃榆钱,年年有余钱。榆钱还有许多保健功效,中医认为多食榆钱,可助消化、防便秘、清热祛湿、健脾消肿。所以,一到榆钱成熟,人们争相采摘。榆钱的吃法有很多种,可以往发好的面里揉榆钱做成榆钱馍,也可以把榆钱拌上面粉蒸着吃,还可以生着吃。记得小时候,经常像小猴子一样爬到树上,大把大把捋下来榆钱,直接往嘴里塞,甜丝丝的,嘴里弥漫着春天的味道。
爷爷在世时常说,这棵树救过我们全家人两次命,家里再困难也不能卖掉它。1942年夏天,豫北地区连续几个月大旱,夏秋两季庄稼几乎绝收。因为饥饿,我们村里每天都有出去逃荒、要饭的,好多人再也没回村,饿死在外地了。爷爷说,那时我们家里地多,有些余粮,但爷爷弟兄四个,都是半大小伙子。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到来年春天,眼看着囤里的粮食越来越少,曾祖母就把榆树上的榆钱搀点面蒸着吃,吃了好多天,总算保住了全家人的命。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浮夸风导致全国粮食短缺,再加上自然灾害,爷爷说,人都饿得前胸贴后背,浑身浮肿,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晕倒,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棵老榆树又一次救了我们全家。
现在人们再吃榆钱馍,不是为了保命,是白面馒头、大鱼大肉吃腻了,想尝尝鲜,吃个稀罕。年年春天,母亲都给我们蒸榆钱馍。母亲做的榆钱馍特别好吃。
母亲每次蒸榆钱馍,都把榆钱清洗四五遍,洗得干干净净,沥干水分,放入盆中,掺上食用油、盐、鸡精、十三香,搅拌均匀,揉进发好的面团里。和好菜团后,再拉成长条形状,切成一个个馒头,再醒上十来分钟,就可以上锅蒸了。半个小时后,热腾腾、香喷喷的榆钱馍就可以出锅了。
吃榆钱馍也有讲究,在上锅蒸的那段时间,母亲用蒜臼子把蒜和青辣椒已经捣好,再淋上芝麻油,等馍一熟,蘸着吃,实乃人间美味。
看到榆钱馍,想到母亲用镰刀钩榆树枝、捋榆钱的情景。母亲早已过古稀之年,但还时刻想着她的儿子、孙子、重孙子。唉,儿子年龄再大,在母亲眼里永远是孩子,永远是她心头那份最重的牵挂。